
2023.06.12:留著這篇只是為了記錄,跟欣賞林奕含的文字之美。
我對於受害加害者,對於創傷的角度已經改變。因此裡面有很多東西已然是過去。
-------------------------
幾天前,一位26歲的女孩離世。
在此之前,第一次聽到她的消息是她結婚了,在婚禮上講述自己罹患憂鬱症的心路歷程。
第二次,是她出書了,到處接受訪問。
第三次就是這個消息。
過去我對於患有心病走不出來的人,有著很膚淺的認識,認為那是說到底是一種懦弱,一種自溺。
我對於自己的膚淺自知嗎?或許其實是知道的。
但我把它包裝成一種堅強、一種粗心。
「因為人不願意承認世界上確實存在非人的痛苦,人在隱約明白的當下就會加以否認,否則人小小的和平就顯得壞心了。在這個人人爭著稱自己為輸家的年代,沒有人要承認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輸家。那小調的痛苦確實與幸福是一體兩面:人人坐享小小的幸福,嘴裡嚷著小小的痛苦——當赤裸裸的痛苦端到他面前,他的安樂遂顯得醜陋,痛苦顯得輕浮。」
一本探討童年創傷的書提到,有些受害者會埋葬那些痛苦的記憶到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
有一段文字讓我印象深刻,是一個已經結婚生子的女人,在一個下午偶然看到自己女兒紅髮的一道閃光,才猛然回想起自己童年的巨大創痛—她的父親強暴了她跟她朋友,再殺了她朋友。
她童年好友的紅髮。
又猛又急。
從無到有。
「那是房思琪第一次失去片段記憶。」
我的醒悟,我一眼瞥見的那個地獄。
第一眼,是作家的離世。第一次,我發現自己周遭不遠處,的確充斥著我從未注意過的奸惡,進而發現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名性騷擾受害者卻不自知。
我怎麼就沒想到呢?
當那個我信任的長輩的手伸過來後,我沒有說出去。那是對中年男子的悲憫,還是懦弱;是我的心智健壯如牛,才讓我始終未曾再想起這段人生插曲,還是因為我太纖細,才必須停止聯想下去。
我早忘了這件事。沒有記憶,沒有創痛。
我看到新聞,才想起來那隻手。但他沒有減損我對人性的天真。
想來我該是健壯如牛的那種。
第二眼,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是我的那道閃光。
作為一名細膩、尚不知感情為何物,卻又早熟到已能以超齡想像理解情慾高度的少女,房思琪為什麼不呼救?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回虎口?事隔多年又為什麼不放下?
她的情緒漩渦—那混亂又疏離,卻又字字血淚的控訴—誠如所言,是「標本」,一字一句的痛楚,被描繪下來,供養起來,供人觀看。
我一字一字走過,才終於得到這些疑問生於渾沌中的種種答案。
我看著這個標本,注視著它的駭然瑰麗、鬼魅沉沉。
然後在某個瞬間,
猛然醒悟我看著的也是我自己的標本。
當時回家的時候我還是哭了。
我把這件事在日記上寫下。
儘管如此,後來這頁還是被撕下來,撕得粉碎丟進垃圾車。
「最終讓李國華決心走這一步的是房思琪的自尊心。一個如此精緻的小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這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傷人傷己的針,但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
他後來成為我的第一個男朋友。
在我心中他真的不是個壞人,所以我後來也忘了這件事。
要把初戀解讀成那樣有汙點的事,我往後三年半從沒試過。
直到今天,讀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這件事才又猛然回到我的腦海中。
那其實是一件太過份的事嗎?
那就叫做性騷擾了嗎?
所以我被性騷擾過嗎?
分手後,我也有留意過很好的男生。但我直覺會想:「他太好了。他太乾淨了。」
我甚至沒意識到我為什麼會覺得他「太乾淨」,而又為什麼那會是個問題。
「小葵,小葵沒有不好,事實上,小葵太好了。...我很可以喜歡上他,只是來不及了。也並不真的喜歡那一類型的男生,只是緬懷我素未謀面的故鄉。」
紅髮間一閃一閃的光芒,我潘朵拉的盒子。
我想起來了,也終於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我終於明瞭我並非健壯如牛,才可以對於性騷擾毫無傷痛。
而是當對你做這件事的人說他愛你,他是因為愛你才做這件事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才會是真正見骨的一刀。
「對於一個即使是最親密的人,對他說出我小時候愛上了強暴我的人,對她來說是非常非常困難。這不是關於被誘騙性侵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愛上誘姦犯的故事。」
我們搖旗吶喊必須跨過如同鯉躍龍門的難關,都是不牽涉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難關。大衛與歌利亞,人人歌頌的無畏力量,如此非人,如此純粹,不牽涉何謂羞恥,不牽涉何謂純潔,不牽涉何謂不知者無罪;不牽涉剔透真心,不牽涉自己可不可愛,不牽涉那險惡業火中有沒有自己的難辭其咎。
髒掉的不能變乾淨,髒掉的只能走下去,把深淵背在身上,接受那是自己的一部分,非常隱晦地。
你不會因為如此隱晦的堅強成為更好的人,只能祈求以如此隱晦的堅強而勉強完整。
「我寧願大家承認人間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
當最暴力的已經跟最珍貴的緊密交纏,凡人只能在往後日日裡,往復折返,絕望地來來回回。這故事裡沒有巨人,沒有超越,沒有和解,只有眾生不屑地隱晦。
「這是老師愛你的方式,你懂嗎?你可以責備我做得太過,但是你能責備我的愛嗎?你能責備自己的美嗎?」
因為你太美,因為我的靈魂如此軟弱。
所以我愛上的人,當時其實不是為了愛我才這麼做?
「如果這是愛情,為什麼覺得暴力?為什麼覺得被折斷?為什麼老師要一個女學生換過一個女學生?如果這不是愛情,那滿口學問的李老師怎麼能做了以後,還這麼自信、無疑、無愧於心?」
呵早熟少女的驚人純情,內心過於冰雪能直指萬事隱晦本質,卻為此灼灼目光必須踐踏過所有可以確保安全的社會體制—那些所有妳不屑一顧地路標,不過標誌著通往庸俗幸福的羅馬大道—如果知道什麼是假的,又怎麼能假裝那些是真的。所以妳不要那些東西,而只要那些妳能確保為真,乾淨體面的精神食糧。
問題是—或許是最危險的那個問題是—妳的珍寶最終只是妳而非他的真相。
最終,妳對每件事物的完美主義,明明只要伸手就能得到幸福卻選擇辛苦清醒的完美主義,見過一次地獄後,成了一把沾血的雙面刃,從此小小的幸福更再不能是天堂。七門火獄非人的折磨,相較於偽善卻如此誠實,妳無法放棄它。
第一時間,我只感受到一股憤怒,想讓那個人知道我終於明白他對我做了什麼,我對自己做了什麼。
但很快的我也會意過來,那都沒有意義。他的道歉對我而言已經沒有意義了。
「書裡那個老師的原型人物,我常常跟我的醫生說,萬一那個人哪天老死了、壽終正寢了,我會輕視自己一輩子。我不是生來就會仇恨別人的人,可是我確實地想要物理性地傷害他,但我做不到。」
這時我才懂了她說這句話的意思。
這件事早就跟他無關了。
當他說出:「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麼感覺而已...以後不會再這樣了」時,這件事就與他無關了。
從那時候開始,就只與我有關。
今天我走在路上時,想著我後悔睜開雙眼了嗎?我會希望自己仍把這件事丟在記憶之海嗎?或是偶爾想起,但繼續把它解讀成一個對於真愛曾經的付出。
「我是痛苦的神童⋯⋯我的問題是,人類需要這樣的知識嗎?需要了解,那麼極端的痛苦與真相嗎?」(《永別書》)
尤其如果那是我切身的真相呢?
「我現在讀小說,如果讀到賞善罰惡的結局,我就會哭,我寧願大家承認人間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我最討厭人說經過痛苦才成為更好的人,我好希望大家承認有些痛苦是毀滅的,我討厭大團圓的抒情傳統,討厭王子跟公主在一起,正面思考是多麼媚俗!可是姊姊,你知道我更恨什麼嗎?我寧願我是一個媚俗的人,我寧願無知,也不想要看過世界的背面。」
「我希望任何人看了,能感受和思琪一樣的痛苦,我不希望任何人覺得被救贖。我要做的不是救贖誰,更不是救贖我自己,寫作中我沒有抱著『我寫完就可以好起來,越寫越昇華』的動機。寫時我感到很多痛苦,第一次書寫完成、來回校稿的後來是抱著不懷好意與惡意在寫。」
「我希望看的人都可以很痛苦,我是個惡意的作者。房思琪發生這件事的重量是,即使只有一個人,那個重量就算把它平分給地球上每一個人所受的苦,每一個人都會無法承受。」
口吻如此無情。
但當看到書中這段文字時,我看到的是這個飽受磨難的年輕女孩,故作無仁的善意:
「怡婷,妳才十八歲,妳有選擇,妳可以假裝世界上沒有人以強暴小女孩為樂,假裝從沒有小女孩被強暴,假裝思琪從不存在,假裝妳從未跟另一個人共享奶嘴,鋼琴,從未有另一個人與妳有一模一樣的胃口和思緒,妳可以過一個資產階級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裝世界上沒有精神上的癌,假裝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有鐵欄杆,欄杆背後人人精神癌到了末期,妳可以假裝世界上只有馬卡龍,手沖咖啡和進口文具。但是妳也可以選擇經歷所有思琪曾經感受過的痛楚,學習所有她為了抵禦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從妳們出生相處的時光,到妳從日記裡讀來的時光。妳要替思琪上大學,唸研究所,談戀愛,結婚,生小孩,也許會被退學,也許會離婚,也許會死胎,但是,思琪連那種最庸俗、呆鈍、刻板的人生都沒有辦法經歷。妳懂嗎?妳要經歷並牢牢記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緒,感情,感覺,記憶與幻想,她的愛,討厭,恐懼,失重,荒蕪,柔情和欲望,妳要緊緊擁抱著思琪的痛苦,妳可以變成思琪,然後,替她活下去,連思琪的分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就像思琪從未能夠進入結構,她寧願可以進入結構,寧願當一個無知到進入結構的人。她寧願沒有讀過書,沒有讀過《第二性》、《性別打結》,她寧願『讓男人養她』、『買名牌包包』,她寧願做這樣的人。但不是,她讀過,她了解一切,她還是只能從另一個角度『讓男人養著她』。」
「妳可以把一切寫下來,但是,寫,不是為了救贖,不是昇華,不是淨化。雖然妳才十八歲,雖然妳有選擇,但是如果妳永遠感到憤怒,那不是妳不夠仁慈,不夠善良,不富同理心,什麼人都有點理由,連姦污別人的人都有心理學、社會學上的理由,世界上只有被姦污是不需要理由的。妳有選擇——像人們常常講的那些動詞——妳可以放下,跨出去,走出來,但是妳也可以牢牢記著,不是妳不寬容,而是世界上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怡婷,我請妳永遠不要否認妳是倖存者,妳是雙胞胎裡活下來的那一個。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當成美德是這個偽善的世界維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氣才是美德。怡婷,妳可以寫一本生氣的書,妳想想,能看到妳的書的人是多麼幸運,她們不用接觸,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
兌說,原本她覺得林奕含是個渾身帶著黑暗能量的人,但看完了這本書後,她覺得她其實是黑天使。下筆的時候充滿痛苦,但試圖給世界的,是用血換得的一點溫柔。
「這不是一本憤怒與控訴的書。思琪充滿柔情,心中是有愛的,有欲望的,甚至是有性的。它不是一個女孩子關於被誘姦的故事。」
我寧可解讀成這是思琪最後的大愛,描繪一個血肉之軀如何失去真正意義上的生命,要給整個社會一個警醒—殺人的真義在教養跟安適之下是如何被集體埋葬。
能夠原諒嗎?一個一個的房思琪,是結構的漏網之魚。結構能夠原諒個人,但個人能夠原諒個人嗎?
「我知道站在長遠的歷史來講,確實會新生,我這本書可能有人可以得到警惕,有人也許得到安慰,但我所知的經驗,就是他們沒有了,永遠不敢出門,他發瘋了,如何跟我說有新生?如何告誡世人房思琪成了一個教訓?這樣太殘忍了,我不能和解。」
「包括這件事情的本質,包括我很多年針對它的思考──一個人不再長大,一個人被自己的人生留在原地,一個人是自己的贗品,種種,都是我深信不疑的。」
「老實說可能有點悲觀也像假的,但是真的,我沒有活著的實感,有時候我會覺得,在很久以前第一次自殺時,我就死掉了,我知道這聽來很虛假⋯⋯真正的我,在過另外一個比較幸福快樂的人生。」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少女揉合了早熟與過於純真的禁忌之地。「比處女還處。」那是奕含筆下的形容。
「她的『快樂』是帶有引號的快樂,她知道那不是快樂,可是若她不把那當作快樂的話,她一定會活不下去,這也是我覺得很慘痛的一件事。」
是囚於情慾的魔花,還是遠凌於眾生妄想之上的純淨?那是怎麼樣的初戀?又是屬於誰的樂園?在我們眼睛拒絕注視的陰影處,有人正承受那倖存的痛苦。那裡必須是個樂園,否則彼岸花無法忘情渴飲鮮血繼續綻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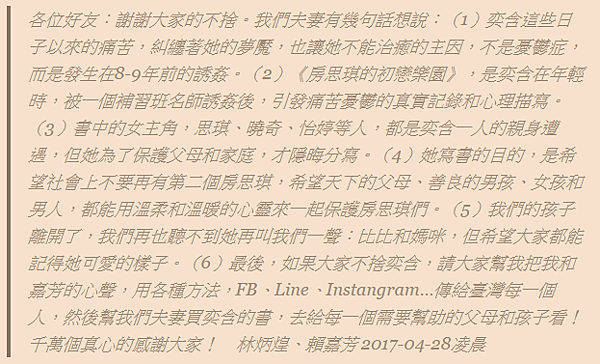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林奕含:寫出這個故事跟精神病,是我一生最在意的事
林奕含:「這個故事摧毀了我的一生,但寫作的時候,我很清醒地想要達到一種藝術的高度。」
後記於04/30:今天跟朋友們聊天,大家說道:自殺的人真的要想到自己這樣做會帶給愛的人多大的傷痛,這樣又會造成多少人群起效尤。
要是以前的我一定忙不迭地附和了。但今天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只覺得心好痛。
得不得體啊,適不適宜啊,結構的漏網之魚,美善社會的害群之馬。如果妳被傷害了,請不要忘記妳的教養,請不要忘記妳的責任。這就是我們,這就是我。難怪她說不出口。
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啊,不是誰的誰,不是為了圓滿誰,不是為了讓誰舒服。憐憫其他人為她的死受害的同時,如果這一點點的悲憫,能夠在生前就給她的話,該有多好。
她拚盡全力,我們只要坐著評論她的努力;她獻祭自己,我們卻在祭壇前竊喜還好自己對或許存在的神更虔誠。
某種意義上,林奕含救了我。我原本還會麻木很久,自以為是很久,但她真的救了我。
後記於05/01:
其實我還是抱持著沒看這本書前的看法:要不要走出來取決於受害者自己的選擇。
這本書只是更讓我可以理解她選擇同歸於盡的原因。
過去我會覺得:既然她自己不想好起來那就不要怪別人。但現在我明白受害者選擇不好起來是一個私人的選擇,不代表就是比較自私,比較不善良。
或許是他的傷痛也同時是他個人重要的回憶;或許忘掉這個傷痛對他而言代表背叛;或許忘掉這個傷痛他認為是助長不公不易;或許真的就是他在大腦的生理結構上沒有辦法承受(家族病史等)。旁人無法論斷,也沒有資格代他決定。
朋友還是很不能接受這樣的解決方式,她對這件事情最大的疑問是:如果她自己不走出來,我們要如何幫助這樣的人?
其實當她提出這個疑問的時候我也傻了一下,我還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的看法是,能做的就是不要想作為外人在這件事中真的能幫到她什麼了。
不要為了她拒絕走出來生氣,不要為了她對你的幫忙不感激生氣,不要為了在這件事中妳不能有用而生氣。
她已經很辛苦,旁人能做的最好的第一步我覺得就是不要再試圖跟她要東西。
更進一步的話,或許就是試著理解她的內心。
奕含的父母、先生和老師面對她的選擇,所展現出來的尊重和理解,對我來說是很令人敬佩的。在那樣的愛中展現了對個人慾望不可思議的自制力。
個人的痛苦終究只能個人承擔。
光是要在漫長的復健過程中反覆力行這樣的修養,我覺得就已經是陪伴者很很大的考驗了。
後記於05/05:
深深覺得一個人能不能得到幸福(或者姑且稱之「世俗的幸福」),跟這個人聰不聰明不是關係太大(聰明只要夠用就好),而是跟這個人夠不夠社會化有關。
除卻金錢,社會運行是透過許多隱形的貨幣,交換在閒語、虛榮以及心照不可宣的恐懼中。太過純粹,甚或在思想上太過超齡的人,反而會沒辦法成為這個體系的贏家。
太過純粹的女性是尤其危險。
如果意識到這些東西虛偽的一面的女孩,不能在心甘情願地回到這個交易體系中,那麼她就不會是不能得到幸福,而是不能再更不幸了。
後記於05/24:
昨天看到《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這本書。書扉上寫著:
「所羅門諾瑟普(Solomon Northup),美國黑人,1808年在紐約州密涅瓦鎮出生,1864年至1875年間去世。
1841年,他在紐約被人綁架,被販賣成為一名奴隸;
1853年被解救后,他成了一位廢奴主義者,並寫作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為奴十二年》。」
這讓我想到最近跟一些朋友聊到房思琪這本書時,有不少人對於這本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以作者的精神狀況,內容可信度跟它掀起的波瀾根本不成正比。
讀到所羅門的回憶錄時,我突然覺得,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過於嚴苛。
市面上有多少回憶錄啊,但我們討論相關問題時,很少牽涉到回憶錄的真實性,只因為比起這本書,那些故事跟原諒或什麼崇高的東西更有關嗎?更何況作者已經開宗明義說這是小說了。
重要的是那樣的剝削究竟可以對人造成怎麼樣的精神傷害。
重要的是還有多少人對於自己本來可以避免的傷害一無所知。
知道其實有些事情不該被默許發生在自己身上;知道即使這個人不是需要用「壞」來形容的人,他當下的行為就叫做「暴力」;知道自己身為女性被教導要慷慨,但生氣不會減損那樣的慷慨。
小說就是小說。
但這不影響它的重要性。
後記於06/10:
今天讀《當呼吸化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寫道:
「《美麗新世界》奠定了我剛出生的道德哲學,成為申請大學作文的主題,我在文章裡主張:快樂不是生命的價值。」
這跟我最近正在形成的看法不謀而合:要問自殺是不是有罪的,那就要先自問對你而言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若生命的意義不在『幸福』或『無傷』,那便不能說自殺的人是罪人。
後記於06/12:
今天看了岡田尊司的《依戀障礙》,突然想補充一點05/01所說的。
不要認為把一份傷痛跟自己人生的其他部分切割乾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舉例來說童年的創痛,父母疏離、自殺等等,都會造成一個人深刻的創傷。甚至要花一輩子的時間去挖掘療癒。
幸運一點的人,即便早早就知道自己的問題並求助,還是常常會在人生中的某個時刻突然驚訝於自己的某個部分原來還是未解碼的。
這些創痛跟我們來這個世界上的源頭有關,也跟我們認為本該無條件愛我們的人有關,要談切割,談何容易,動輒分筋剔肉的。
我相信其他跟自我價值深有牽連的痛苦皆如此。
後記於06/26:
昨天讀到《齊瓦哥醫生》中,拉娜講到自己的這一段:
「我像什麼樣?我身上有些東西破碎了,在我的整個生活中有些東西破碎了。我懂得人生太早,我是被迫懂事的,我是通過一個自以為了不起、年紀較大的寄生蟲的眼睛從最壞的一面—廉價的、歪曲的一面—去看人生,那個傢伙任何便宜都要占,並且不管什麼壞事想到就幹。」
「我想的正是這種美。我以為,剛看人生時你所想像的必定是完整無缺的,你所憧憬的必定是天真的。可是那正是我被剝奪的了。
如果從一開始我不曾透過另一個人庸俗的眼光去看穿人生,我可能發展出一套我自己的人生觀。
問題還不只於此。就因為這個不道德、自私的不足取的人物在我幼年時闖入我的生活,當我日後嫁了一個他愛我我也愛他的真正了不得的人時,我的婚姻才被摧毀。」
後記於03/20:「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關乎權力。」—王爾德
後記於2020/03/18:
在醫院空閒時又重讀了一次。
突然發現角落一句上次看時沒有發現的話「以前,我知道自己是特別的小孩,但我不想以臉特別。我只想跟怡婷一樣,至少人稱讚怡婷聰明的時候我們都知道那是純粹的。長成這樣便沒有人能真的看到我。以前和怡婷說喜歡老師,因為我們覺得老師是『看得到』的人。不知道,反正我們相信一個可以整篇地背《長恨歌》的人。」
哭了。突然理解到我跟L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我死也要緊緊抓住的東西,放棄了盲目了周圍所有溫暖與虔誠,只因為我相信這個人「真正看見」了我。
如果我那時候早早很乾脆地相信了錢、愛慕、社會共識與虛榮,或許我根本不會愛上L。
然後一步一步,妳見證人可以怎樣去扭曲話語、可以一點不愧疚地瞇起眼檢舉妳的一言一行但嘴裡說愛妳。
而在不能快樂的時候,妳根本不值得一想,不值得一提。
所以,已經四年了,還是覺得很噁心很空洞:「每次思琪在同輩的男生身上遇到相似的感覺,她往往以為皮膚上浮現從前的日記,長出文字刺青,一種地圖形狀的狼瘡。以為男生偷了老師的話,以為他模仿、習作、師承了老師。她可以看到欲望在老師背後,如一條不肯退化的尾巴—那不是愛情,可是除此之外她不知道別的愛情了。」
有一次跟一個男人單獨在一起時,他看出我的緊張。我囁嚅地跟他道歉:「抱歉,是我自己的問題,我的確相對起來更相信女人...」
他連忙澄清:「我對妳沒有任何欲望,只是覺得妳是美麗的生靈。」我看著他的眼睛,想在裡面找出一絲攻擊性。那些自私的殘忍的念頭,我要怎麼相信他?我的確不相信。
我發覺自己在觀察其他情侶時會試著去找到一個男人真愛著一個女人確鑿的證據,不是性、婚姻或甜言蜜語。
他愛著她嗎?還是他其實是要剝削她?我要怎麼相信他的行為或他的話?
當有一個人對你做出這樣或那樣的事,那是愛嗎?還是不是?
我小心地把這些困惑我的部分挑出來,然後分類、歸位,放的老遠,抱著膝蜷在沙發上,和他們遙遙對望。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後來決定跟原本生命中的一些人保持距離,我不想混淆我很努力建立起來關於愛的定義。
我喜歡跟非常確定對我沒有任何興趣的男人待著的平靜,但我還是克服不了嗅聞到異性興起一絲欲望的波瀾。我在裡頭會暈船,不知道怎麼不感到危險跟作嘔。
後記於03/20:取自林奕含臉書
我是非常迷信語言的魔術的人
當一個人對我說「妳完全可以相信我」
我真的就會開始完全相信她
因為我自己對文字是異常忠實的
「我是非常迷信語言的魔術的人」
簡而言之──
「我是非常容易被騙的人」。
我不知道旁人有沒有因此理解了她的幻滅。
但我想到L。我覺得我因此理解了我的。
他人常常難以理解的,我對情感異乎尋常的忠誠和仰望。
於是每次都到人走光了,我還在原地愣愣的流淚。
想到媽媽說的「妳就是一喜歡就喜歡過頭。」
才發現在有口無心的所謂社會裡確實是我太容易動情。
後記於06/12:
「這是個多麼可怕的魔力圈啊!如果柯馬羅夫斯基闖入拉拉的生活只會引起她的厭惡,那她必將反抗,並從他懷抱中掙脫出來。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這個頭髮班白、年齡可以做她父親的漂亮男人,集會上受到歡迎,報紙上經常讚揚,竟把金錢和時間花在她身上,稱她為女神,帶她看戲、聽音樂會,即所謂『開發她的智力』,對女孩子還是很受用的。
她還是穿著灰褐色連衣裙的未成年女中學生,學校惡作劇的秘密參加者。科馬羅夫斯基在馬車李、馬車夫的眼前或在劇院幽暗的包廂裡,當著全體觀眾的面大膽向她調情。科馬羅夫斯基大膽的舉動喚醒她心中的小鬼,也想模仿他。
中學生淘氣的衝動很快就過去了。留在心裡的是灼傷,是對自己的畏懼。由於夜裡睡不著,流淚,頭疼不止,背誦功課的勞累和身體的疲憊,她白天老想睡覺。」—《齊瓦哥醫生》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醫學
醫學